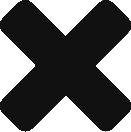臉
母親傳了訊息給我與哥哥,告訴我們她上一週忽然得了顏面神經麻痺。她臉部右半邊的眉毛橫豎了起來,嘴角往上歪斜,閉眼時右邊的眼睛也無法完全閉合。訊息的照片裡,母親沒有太多的表情,深邃的雙眼盯著鏡頭,有些肅穆,但那歪斜的嘴與眉又似乎組成了一個詫異的微笑。似笑非笑的臉,有些詭譎,有些愁苦。
我的生命教育
傍晚回到家,匆匆忙忙地開始切香菜、搗蒜頭,想要做一碗涼拌酸辣粉。邊調理著醬汁,邊檢查訊息,G說她再過五分鐘就會打來了。
G是我在東岸唸博士班時最親近的摯友。她來自紐約上州一個貧困的家庭,母親在超市當收銀員,繼父這一兩年動了幾個大手術而行動不便。其實,有關G的家庭,我知道的細節並不多,模糊地明白他們一家人在貧窮與毒品之中沉浮,辛苦地維繫著家庭的功能。這樣的家庭,有愛,有歡笑,也有傷殘。
Oct. 23 2022

星期天的早晨,吃完早餐,我們到附近的一處公園散步。原本只是想說看看濕地與山脈,認識一下附近的步道,沒想到卻邂逅了一個大鹽池。這個公園位在舊金山海灣的最深處,海水從狹窄的金門大橋灣口進來以後留下營養物與鹽,因而造成鹽分較高的濕地生態圈。漲潮時從海灣湧進乾淨的水源,退潮時潮汐又會帶走這裡的污染物,這裡的生態圈因而有足夠的土壤養分支持許多耐鹽的植物、水鳥。
回頭
那一天,在太浩湖 (Lake Tahoe) 附近的一座山頭上,我們看到了雪。正確地說,應該是冰雹——六月中旬時無聲且迅速的冰雹,重力加上冰凍的雨點,輕打在我們的衣服上。那個時候大概攝氏六、七度,其實沒有很冷,是我們的身體曾經熟悉的溫度。
乘車的夜晚
回到賓州小鎮時,已經將近晚上七點了。聽朋友說前幾日有大風雪,回程的路上除了沒有路燈照明的暗夜,印象最深的是下了Uber計程車,腳底踩到停車場路面上那堅硬且滑的冰。從鄰近北回歸線的亞熱帶海島,到沙漠沿線的城市,再回到長住近七年的山谷小鎮,見到白皚冰雪時,有種旅程結束,準備好面對漫漫長冬的感覺。
立冬
睡前沉澱,翻開電子書閱讀器裡靜置許久的徐國能的《第九味》。斷斷續續地閱讀,像年幼時期吃飯一樣,想到時就扒個幾口,只是讓我分神的不在是晚上六點半黃金時段的卡通,而是為能完成生活的各種勞動,二十歲晚期必須看盡的風景。
前幾日讀完了令我意猶未盡的〈雪地芭蕉〉,全篇散文以第二人稱書寫,是作家徐國能對一位「擁有偉大生命與理想,卻未能相互完成的老師」的紀念。散文的開頭是這麼寫的:
七年
不知不覺搬進來新家也整整兩個月了,街角的老公寓靜靜座落在林子一旁,晚上開窗時總是可以聽見各式蟲鳴,就這樣默默展開了在賓州的最後一年。
第七年的感覺很奇特,忽然覺得時間慢了下來,與身邊的物事有種離異感,偶爾像是在看電影一樣觀望周遭,很是在乎,心思有所牽引,又能保持一點距離,讓物事像情節一樣緩緩消逝。與芝麻一起搬進我們的一人房以後,覺得很安定,很珍惜與她還有自己的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