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香吟的《其後それから》是一本沒有前言自序與推薦序的書,不加修飾地靜處於這個世界。極簡的幾何圖形與灰白色調構成的封面,有種素靜沉潛,沒有打算向誰多做任何解釋的感覺。故事的第一頁就將讀者帶進敘事者與好友「五月」初見彼此的青春現場:活動中心的褚紅色大門,知識殿堂的沉思與喧鬧,生命,就在這裡開始成為自己。兩位摯友在藝術與寫作的道路上,像是為彼此引燈,卻無法預見出了校園的現實即是各種跨不過去的坎,自我認同之路原來是那樣曲折。
《其後それから》是大學好友易嫺推薦給我的書。會談到賴香吟,其實是那時候我提及我讀了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並且希望能夠把《手記》與情慾寫進論文裡。1995年,邱妙津在巴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箱手稿與日記飄洋過海被交到生前好友賴香吟手裡。《其後それから》書裡無名的「我」作為敘事者,還有化名為「五月」的摯友,像是映照了現實生活裡曾經是摯友的賴香吟與邱妙津,卻又刻意保持了虛構與文學的距離。好像唯有如此,賴香吟才能在不遠不近的地帶重組好友自死之前與之後的記憶片段。如同無名的「我」提到,經驗像個萬花筒,每一次轉動,都會重組其形狀與花樣。《其後それから》沒有企圖「還原」任何事故以及其中的拉扯,而是透過不同體裁的書寫(第一人稱、第三人稱、診間對話、獨白、閱讀筆記、日記),從不同角度映照摯友與青年時代的消亡,同時回溯被劇烈劈開的生命中長出的硬刺與柔軟花瓣。
雖然是因為讀了《鱷魚手記》的關係而接觸《其後それから》,卻在閱讀過程中明白,這不是一本全然關於「五月」或是作家邱妙津的書,而是無名的「我」的餘生敘事。重組回憶與重訪好友的逝去現場,「我」也必須在事件之後重新尋覓自己的寫作聲嗓,拾起筆詮釋自己作家的角色。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摯友自殺後,敘事者「我」成為其作品中介人,謄稿編輯,簽字出版,成為五月對外的發聲者,卻失去自己在文學上的位置:「我失去了自己的角色,成了一個關係人,作品不分青紅皂白地都被做了關於五月的聯想與影射……」
有趣的是,無名敘事者「我」既知道自己終其一生都要面對旁人對於她與「五月」的臆測、穿鑿附會,仍決定將她對於「五月」的所思所想以及她自死之前與之後的片段記憶,端程於讀者面前。無論是讀者、敘事者「我」、還是作家賴香吟本人,都透過《其後それから》望進一位青年之死所造成的虛空黑洞。摯友之死。作家之死。愛人之死。青年時代的提早消亡。我們與這個事件有不同的距離,看見的也是不一樣的「五月」(被閱讀的「五月」、「我」所認識的五月)。作為讀者,我也必須拋棄學院的訓練,評論的眼光,也就只是聽著,讓死亡造成的空蕩模糊自己的感受邊際。時遠時近地,跟著敘事者對所謂的「生活」、「現實」以及「死之抽象與成真」做出各式的提問。
生之限制,語言之限制
讀到書的後半,覺得《其後それから》吸引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拒絕去歸納或是還原事物的成因。無論是引發「五月」在最後一刻選擇自死的導火線,或是敘事者「我」與「五月」之間所經歷過的「大破滅」,還是「我」坐在諮商診間針對寫作停擺或是摯友消亡,文字密碼裡始終沒有透露出個所以然。諸多事件沒有一個關鍵的成因,沒有所謂的始末,拒絕被定義,拒絕被命名。
並不是不願意說明白,而是語言也有它的侷限,困境與失樂園的形成也無法用線性的常理去理解。《其後それから》書裡的「五月」以及現實生活中的作家邱妙津都在自死之後的幾年內成為台灣「同性戀」文學的指標人物,她們的死像是製造了一段傳奇,為常規社會不能觸及的精神與情感宇宙獻祭,也確立了她們的文學形象。但如同賴香吟寫道,「同性戀」這個說法最終是個「外加而遲」的詞彙:雖然它讓敘事者「我」在後來稍微釐清了她與「五月」的關係以及纏繞「五月」的問題,但它不能夠用以解答事件的全貌。 有一些更深邃、更細微的情感,原始的問題,瞬息生滅的意念,是再怎麼抽絲剝繭,都不能釐清,也沒有理由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讀著《其後それから》的這陣子,我也同時在讀美國性與性向研究學家伊芙·赛菊寇 (Eve Sedgwick)的《暗櫃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這本出版於1990年的書旨在檢討自1970到90年間熱烈展開的同性戀身份認同運動傾向把「出櫃」當作單一的抗爭策略,許多參與運動的人士認為只要人們願意「出櫃」,願意擁抱所謂的「同性戀」身份,異性戀霸權就能夠因此瓦解。但是赛菊寇告訴我們,「出櫃」作為抗爭的手段預設了「同性戀」作為身份與族群認同的單一性,同時也假設同性戀身份認同能夠解鎖個人生命經驗與情慾的複雜。《暗櫃認識論》不但破除了我們對於出櫃/入櫃、同性/異性的單一、二元的理解,也要我們去正視個人生命的輾轉堆疊、迂迴纏繞。個體經驗的無限複雜,獨一無二的情思繾綣徘徊,是再多的論述與文字都無法言盡的。知識的創造以及認知世界這個動作,是有限的。
雖然《其後それから》與《暗櫃認識論》生發的脈絡不同,兩部作品卻從各自的時空情境去觸摸「限制」的邊際,都想以清明的眼去觀望情感,卻又明白所謂清澈明朗,在智識上不一定是全然可得的。透過「五月」的死,賴香吟在《其後それから》一書中探討了多種限制:死亡作為生命之限制,語言作為瞬息萬狀的經驗與情感之限制,藝術作為表現形態之限制,或是不同生命基調作為彼此發展出情愛之限制。面對這些限制,敘事者「我」並沒有打算要以戰士之姿迎擊或是超越,也沒有絕望憤怒的控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耐心的凝視,目光停駐在死亡造成的無底黑洞,眼見的卻再也不只是截斷與剝奪,還有那緩緩朝著「我」流淌而來,涓絲般細微卻無比潤澤的求生的勇氣。如同賴香吟寫道的:
父親之死對我最大的救贖,就是殘忍而溫柔揭示了生命的有限,死之存在根本性決定了人生的有線與殘缺,任我們如何鑿愜意至於完美並無法改變這有限而殘缺的來臨,如何自棄自絕以睥睨之亦不能使這有限與殘缺有一絲一毫的動搖——這就是答案了,可答案顯現的同時彷彿也有誰蒙住了我的眼睛,筆下自動滑出這樣的句子:去吧,去玩你的吧。
《其後それから》,頁222。
這個在情緒迴圈裡繞了好幾回後才得到的鬆綁,是《其後それから》最令我動容的地方。始終不能面對青年摯友突然的生命截斷的敘事者「我」,從宗教、文學、心理學多面向地去釐清死亡的意義,壓抑創傷甚至幾近要放棄寫作,最後卻因再一次與死亡照面,而啟動了生之慾望。並不是戰勝了,克服了,覺悟了,而是領受了,被接納了,於是能夠以自己的語言再一次細細描繪死亡。 即使再多的語言都不能簡化對逝者的思念,還有作為餘生者背負著的羞恥感,但總是嘗試了。最終,的確是將自己交了出去。一切都會過去。
文學與生之慾望
寫到這裡,也快要把《其後それから》這本書讀完了。過去這個月的許多日子,都是賴香吟文字裡悠悠漫流的 思索陪我度過了慘白寂靜的冬天早晨。書中的人物有著充滿象徵符號的名字(噩夢主」、「樹人」、「五月」),好像要刻意劃清賴香吟本人與她筆下的敘事者之間的距離,也要求讀者隔著一層虛構的薄紗凝望《其後それから》裡頭的情感網絡。但是越到後來,敘事者「我」的聲音越來越清晰,形象越漸飽滿,不再是個旁觀的敘事者,而是能夠向內在沙漠挖掘的作家。即使虛構的名字與拼圖式的書寫創造了文學距離,「我」的聲音與作家賴香吟的聲音卻在最後慢慢地重疊在一起。這不禁讓我思索著,如果最後都是要將自己端程出去,都是要以自剖的形式見證倖存餘生,為什麼又要特意去經營文學的距離?
在摯友「五月」死後對文學大失所望的「我」,幾乎是以放逐自我的姿態重重踩踏文學,遠離寫作。文學觀照了我們所處世界的扭曲與富饒,然而它也聚集了許擁有澎湃心靈之力最後卻消滅自己的作家身影。《其後それから》書裡提到太宰治、海子、顧城,還有做為「五月」腳本的邱妙津——這些親手葬送自己的作家,成為後世的文學傳奇,卻讓賴香吟迫切探問文學作為精神食糧的終極限制。能夠在小說或詩歌中創建另一個宇宙的巨大精神力,發展到最純粹、最極端之時,是肉體無法承受的折磨。有一些不能言明的癲狂,那麼美,卻也直指著絕望與耗損。巨大的精神力,沒有與世界接通,卻將其擁有者推向孤獨境地。
這樣的精神力所創建的文學,激發我們的審美與同理,震盪著我們被枯燥現實鑿鈍的心靈。但賴香吟似乎是要告訴我們,文學所創造的境界,美好的或是幽暗的,不全然是為了讓讀者將自己的形象投射進去。文學不是倒影,不是為了讓我們在裡頭耽讀、錯解。文學的創作也不全然是對殘酷世界的自白,不是孤注一擲、貫徹心靈之力以後,就能將自己交給死亡。
這一份對文學創作與閱讀的體會,或許也解釋了為何賴香吟將事件發生後的所悟所感寫成一部虛實相接的文學作品。這麼樣寫,並不是為了獲得誠實自白之後的救贖,也不是以向讀者傾吐之姿得到治癒。充滿象徵符號的代名詞,萬花筒般轉動的記憶與書寫,作家自己若即若離的身影——文學式的書寫是為了讓自己站在不遠處凝望曾經有的羞恥與困惑,憂鬱與惶恐,用文字將自己托住。於此同時,賴香吟建立另一種文學與死亡,與生,的關係。即,並不是寫完了就獲得治癒,但也不是寫完了就能死去,像是寫遺書一樣——而是寫完了還得繼續活著。活下去。在不能找到解答一切的答案之時,不能全然釋懷之時,依舊活下去,見證其後的變化,並以自己的語言描述、傳遞。
也許,在記憶受創的地方,在生命將盡截斷之處,有一些東西會慢慢地長出來也不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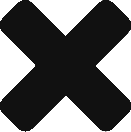

最近也剛讀完其後,偶然間看到你的文章,我覺得寫得真好!
Ya Hsin好!沒想到在這裡寫文章能夠遇到讀者,好開心 🙂 之後也去你的書櫃拜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