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上一次上來這裡寫文也幾個月了,終於走過陰冷漫長的冬夜,能夠曬上三個月濕濕熱熱的陽光。沒有寫網誌的時候,我偶爾寫寫日記,雖然記錄了零碎雜感,卻沒有那種將自己靜置、沉澱,好好地將自己與周遭的世界看清楚的感覺。
幻想自己是一隻灰貓,躺在書房的一方陽光裡,發懶地伸展軀幹,露出肥滿的肚肚。好像能夠相信世界是良善的。
幾週前跟其中一位指導老師到隔壁小鎮喝咖啡。M老師在哲學系任教,研究的是拉丁美洲的去殖民女性主義與現象學,由個體感官經驗出發去探討殖民、種族、帝國思維對個人身體與族群造成的傷害。老師也是位藝術家,她的油畫充滿了心臟與血液等鮮紅的象徵符號,她說她最愛的顏色是紅色。紅色,讓我想到創傷與暴力,肉體的顏色,切割之後流淌又乾涸的血。但看著老M師的紅色粗框眼鏡還有神話性的圖騰項鍊,她的紅色也令我感受到赤子般的熱情與求知慾,她的去殖民女性主義課堂總讓我感到自己與一個更大的什麼接通了。年少時在尼加拉瓜成長的M老師,因為80年代內戰而舉家成為難民來到美國,或許是因為這樣的經驗,老師的哲學系統裡充滿了更大維度的同理,生硬的理論總是被轉化為充滿同情共感的詩的語言。我想這是我在課堂上感覺到被包覆、接納的原因。
在郵件裡跟M老師說了對於未來的的決定,老師說她非常傷心,想要好好地與我聊一聊。
那一天是清朗的大晴天,我們坐在復古老屋改建成的咖啡廳外面,看著眼前綠蔥蔥的小花圃,那一刻覺得自己的生命很渺小,就像眼前容易被遺忘的團團綠葉,很渺小,也很踏實。
這大概是這陣子以來最令我心情盪漾的對話,倒不是因為自己已經做出想要在拿完學位以後離開學界、到業界工作的決定,而是因為從老師的話語跟眼神中,想起我們再也不能在學術與課堂裡並肩走著這件事。
像是從原本的小徑上偏離,走了一條幾年前沒有想過的岔路。這個抉擇其實已經在心裡醞釀了一年半,直到這幾個月才漸漸地以各式現實因素的樣貌,讓我與自己誠實對話,做出選擇。我跟M老師說了一些現實的考量,如工作地點、家庭、工作與生活平衡、身心健康還有就業保障等,老師以她一貫的耐心與深沉聽明白我的決定。
「學術界需要像妳這樣的年輕學者。問題是,妳需不需要學術界?這個地方值不值得擁有妳?」M老師這麼問。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與現實周旋,好像是因為諸多現實的因素導致自己必須在學界與業界之間抉擇,但我心裡總覺得自己其實是被一個更大的什麼吸引過去。一天夜裡沖澡時,水氣朦朧之間,想起目前為止的人生好像都是線性的移動,無論是升高中、上大學,甚至是在念博班的過程中,其實都鮮少有機會停下來問自己究竟想要從現實與生活中獲得什麼。電話裡,笑著跟朋友說,都一個28歲的人了,怎麼好像沒有如此慎重地傾聽自己,為自己做出對自己最好的決定。
疫情之年雖然製造了巨大的恐慌感,也讓原本走到一半的路更加艱辛,腳踩不到地,但卻也讓我停下來,在混亂之中重新審視眼前所擁有的選項。心裡一直對生活與寫作念念不忘,想要與愛的人們、動物共同編織生活的網,想要參與更多公共事務與社群,想要成為自己會喜歡的大人——想要一個能夠成全自己對這一切的渴望的選項。於是選擇了另一條路,就這樣從原本的軌跡上岔開了。
「妳需不需要學術界?」
其實心裡想的是「妳需要什麼?」曾經在一次的失戀經驗中,對方告訴我「需要」與「想要」是不一樣的:我想要妳,但我不一定需要妳。我一度對這樣的劃分感到困惑,覺得是自己對於愛情的態度太天真了,才會把兩者混為一談。那是七年前的事情了,七年之間所經歷的事情讓我慢慢相信這兩者是不需要劃分開來的,看似不一樣的事物不一定是彼此的反面。我可以同時需要、也想要一樣東西,一個人,一群人,一種生活樣貌。
我跟M老師說,我需要與我的伴侶、朋友、貓咪們在一起,想要身心健康,平衡的工作與生活,想要有空間可以隨心所欲的寫作,想要更多時間做社群參與,想要成為自己會喜歡的大人。害怕殘缺的體制、緊縮的空間會把自己的初心與自我認同消磨掉。
「但妳在學術圈目前為止產出的作品與影響是很好的…」
「可是我在學術圈以外也可以持續做出很棒的東西、對人群有正面的影響啊。」
其實不是對自己沒信心,而是越是長大,越感覺的到身體與人性的脆弱,不覺得自己能夠抵擋得過體制的要求,還能夠不屈服、不受傷。想要保有自己多一點,在此時從筆直的大路上拐了個彎。
—
與M老師相處的時光總讓我想起青春時期遇到的幾位老師。十一歲到十五歲是多麽稚嫩的時期,那個時候還沒經歷基測與學測,沒有分級,一個班上總是有來自各種階層、各種背景的孩子。在那稚嫩卻關鍵的階段,我遇到了兩位非常好的老師,分別是國小五六年級的王老師與國中八九年級的莊老師。兩位老師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絕對不會遺落班上任何一個孩子,不論資質、能力、背景,老師都會努力去照顧他們。在菁英主義、能力取勝的大環境底下,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的兩位老師不管做什麼都會確保全班三十幾位同學都能夠共同參與,能力好、資源多的孩子並不會因此得到比較多的關注。老師們讓我知道教育的意義並不是去獎勵那些社會定義為「優秀」的人,也不是去複製「光環」、標舉出能力好的「模範」,而是幫助每一個學生建立社會參與感,發覺自己的能力與頃向,能夠自愛,也能夠愛人。在M老師的課堂上,我總是想起這些事情。那是一種在廣大的知識殿堂裡,你能夠站穩腳步,對自己與他人充滿信任,能夠傾聽,能夠與老師還有學習的夥伴們一起探索,沒有人被遺忘的感覺。
這也許是我這幾年從學者的訓練中得到的最大啟發。不只成為治學的人,更是一個自己必須時時學習、與時俱進、與他人同行的學習者。我問M老師,過去這幾年的訓練,我的學術產出跟我的所見所聞,一定都要在學術界或是學術機構裡才能夠有意義嗎?去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總是強調每一個主體的複雜與多樣性,即一個人不是單一身份與標籤能夠定義,也不是簡單的紀事或是編年史能夠簡述的。
多麽想要繼續探索自己不一樣的面貌。聊到我們都很景仰的去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家,我們相視而笑。
是紅色粗框眼鏡背後那充滿信任的眼神,讓我覺得放心,覺得可以把想要的、需要的都慢慢說出來。
M老師最後緩緩地問:「妳跟我說說看,做完這個決定以後,你心情怎麼樣?是很舒坦、很自在,很開心,還是有點哀傷?」其實每種情緒都有,但是總覺得眼前的風景寬闊許多,有一點點哀傷,可是也是很舒服的。最重要的是,許多事物的決定權又拿回來自己手裡,不再只是以被動的姿態,在極度沒有安全感的環境裡,祈求好運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那就是了!」
—
後記:
這幾天旅行歸來,夜裡翻著《邱妙津日記》,希望能夠進入她的語境與世界觀,好好地把論文最終章寫完。1990年的三月,邱妙津也在日記裡思考著人生中的各種角色,以及它們如何能夠滿足她對於創作與自由的慾望。當時快要滿21 歲的作家寫道:
「也許在這個藝術生命過程中我要經歷各種身份的定位:心理治療師、記者、小說家、電影導演、教授、雜誌主編、社會運動家,但是貫穿這些角色的自我認定和生命基調是相同的,不論我的生命處於哪一刻的橫切面,我的外在身份只關係了我的行動環境和成就對象,但我的內在質地都是以藝術家自許、以藝術生命自責的。」
又邱妙津是這樣定義「藝術生命」的:
「什麼是藝術生命呢?就是不惜擺脫一切束縛自由地去遊歷這個世界、去體驗這個人生、去參與人類社會,然後用藝術的感覺去觀照、凝聚藝術的元素去收攝、以藝術的形式再表現,藝術的基本元素是生命、自由和創造。」
在今天的時空狀態讀這些文字,看見的是一個20歲青年作家的理想主義,一點點的優越,一點點幻夢,對於現實與人生較單一的理解(或是錯解?),乘載著巨大的熱情與執著。
觀照自己,其實對於藝術生命沒有什麼概念,也沒有這種朝著生命噴發的能量與理想,但終究還是很欣賞邱妙津對於所謂「外在身份」的定調,他們是生命的橫切面,而橫切面並不完全展現一個人完整的、終極的生命質地。
這麼一想,走一條岔路、選擇一個不同的角色,也不是什麼太大不了的事情。其實也就是走著,懷抱不同的責任,一路看遍不同的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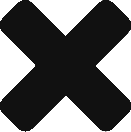

我一直相信,每個做出的決定,都是當下最好的決定!
德蓉!謝謝妳的鼓勵,最近覺得很需要支持。在台灣也要保重,想念妳!
依婷, 我是刁刁(刁颖)。还记得我吗?咱们在Penn State 2019 SI上认识的。之前听宋林说起你打算离开学术界的决定,现在看到你的这些文字,了解到你的心路历程,特别感动。你说出了好多我心里想说的话。我前几天刚向出版社提交了书稿等待外审,算是完成了一个心愿。而我现在也在十字路口挣扎,想要找到下一个人生坐标。看到你最后一句话很释然,不管是有机会留在学术界还是能去到其它业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只是人生路上的一道风景而已。
刁刁!當然記得妳!我好一陣子沒有上來寫文啦,今天登入一下才看到你幾個月前的留言。當初做了這個決定也覺得艱難,但是做完決定以後一直都覺得非常踏實,現在也朝著接下來想去的地方努力著,生活偶有困難,但每一天還是都挺開心的。恭喜妳提交了書稿!我覺得不管有沒有要留在學術界,能夠把自己過去幾年所見所聞跟這個世界分享,都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真的是心願!如果我有機會去明尼蘇達,一定會記得去找你的,也希望你跟你先生都過得好。沒有什麼所謂對的路,只有適合自己當下、讓自己舒心的選擇 🙂
要是猫猫出镜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