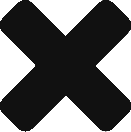從好幾年前開始,就再也沒有認真寫過年度回顧或是新年展望,想著把日常的每一天都過得踏實充盈,也就不太在意跨年,不在意生日。也曾經覺得許下新年希望,就像是在幫自己製造必要的樂觀主義,必要的幻覺,而我們也需要那彩虹棉花糖般繽紛的幻覺,才能夠往前走進下個年度,也才能嘗試活得好。
但今年不太一樣。十二月份都還沒過到一半,就時常有種氣力用盡,望著被白雪覆蓋的平原與山谷,清冷空虛的街道,不知道該拿一切怎麼辦的感覺。生活中各種物事的總和,小至貓咪們待會要吃的罐頭,博士論文裡的一個句子、一個段落,大至持續延燒的疫情,迷茫的未來,奇形怪狀的片段拼湊成帶有重量的斑駁光影,它展現著可愛與韌性,卻也時時提醒著我維持生活品質所需的勞力與時間。將近年尾,時常幻想自己作一頭熊,想挖個很深很深的地洞,在裡頭把自己睡成一個圓。漫漫冬日,竟覺得疫情盛夏離我好遠,盛夏之前的春天,想起來恍如隔世。在家的日子,把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拉得好長好長。
年初的天氣,大概也就像現在一樣,長夜與霜雪,一月與十二月遞接成一個迴圈。我記得自己一月初時的心情,那時候的我每週至少來學校兩天,從圖書館的公車站下了車,慢慢走八分鐘的路到Boucke教學樓,教人生中第一堂文學課。天空或是陰沈死白,或是冬日暖陽,我的步伐總是輕快的。從最一開始教課的過度謹慎,到中期的投入與自在,不知道為什麼會一直把教課聯想成彈奏一段音律,好像把持課程節奏,意境氛圍,真的需要彈琴與聽琴的人相互信任。好幾把琴,好幾個心弦因而能共感共鳴,深入文學意境,深入彼此的話語與意義裡。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教課,即使是比較制式化寫作課也很喜歡。我一直都以為那是因為我喜歡面對學生,喜歡教學現場那種共同解惑、學習的氛圍。直到我開始教文學課,用的不再是系上給我的而是自己編寫的課綱,我才逐漸明白了自己喜歡教課的更深層原因。一個課堂要能夠好,能夠像詩篇般蕩氣回腸,除了仰賴課堂氣氛與節奏的掌控,也需要授業者對於課堂主題有一定程度的執著,執著之時又能把詮釋與質疑的空間教給學生,既要能把一部文學作品誕生的歷史背景、一個理論生發的動機意念傳達出去,又要能讓不同的聲音旁敲側擊,補足且擴大授業者一己之力看不見的角度。我尤其享受這種思考一張一弛的過程,許多時候,教學這件事情於我甚至不止停靠在思考與知識層面而已,它是一個表演:精心設計與編排,卻又仰賴每一個參與表演的人自主詮釋、相互尊重,互動討論之中看見對方從哪裡來,從哪一個生命座標出發。我們既是表演者,也是彼此的觀眾。教課這件事情,也關乎身體,關乎情感,關乎一個課堂能夠激發出的共情與意境。課堂如詩。
・
在共讀共感裡面看見了瑩瑩光火,也導致自己在後疫情時代裡,必須思索如何能夠在不同的場域找到這份如詩的感覺。疫情席捲全球至今,許多人的生活都經歷了劇變,被拋擲出原本的職涯軌道與生活模式。研究所裡許多同事與朋友們,也都開始思索離開學界的可能性,畢竟原本就還沒有從零八年金融海嘯復原的學界,在這一次全球疫情影響之下,狀況更是慘不忍睹。人心惶惶,不時聽到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被裁員的消息,誰因而沒了工作簽必須收拾回家,誰暫離,誰永遠不再回來。生活與職涯劇變,隔離,失聯,保持社交距離,巨大的空蕩無依感,身旁幾位好友也各自因為憂鬱症、恐慌症掙扎著。下午的緊急電話,各種勸說,無解無助,對話的盡頭是急診室。之後是更多的緊急電話,崩潰急促的哭喊聲,深夜十一點開車到隔壁鎮確認朋友沒事,帶她回來我們家住。那一陣子,除了失序,更多的是無解與恐怖。恐怖的不是精神疾病或尖叫哭喊,而是發現哭得再用力、再大聲,也沒有人有餘力幫你。大家都累了。我們只能緊抓著彼此的手,大浪來襲時,努力不被沖散。
能夠躲在家,躲過冠狀病毒,卻不能躲過瀰漫在身邊的精神疾病,言語交談間透露的疲乏感,還有自己的甲狀腺問題與自體免疫。疾病考驗人心,最脆弱的時候,會以為自己再也無法找到生活的實感。沒有實感,沒有詩意。這段期間,想得最多的除了如何把生活過得健康快樂,就是拿完學位以後要去哪裡。一年以前,這曾經是個對於我還有身邊許多朋友而言前所未有的問題,我們都走在傳統人文科研究訓練的道路上,眼光都望向學界,這是體制對於我們的期待,也是我們對自己的期待。我們在這個圈子裡待了好幾年,學習了特定的文化,習慣論述與知識的生產,習慣以思考的吸收與產出衡量自己,忽然要想像自己離開學術圈的樣子,那是何其困難。對於明年秋天就要開始找工作的自己,這個問題既魔幻,又真實。許多夜裡發呆,想起未來,把自己想進一陣迷茫白霧裡。
徬徨失序,卻也是思緒竄流聚攏的時刻,我因為時常處在無解狀態,又開始回到寫作。再怎麼困頓,內心仍然有想要把自己活得好的想望,會覺得能夠用在課堂與學生身上的那份柔軟,應該也用在自己身上才是。想要在思考與互動中找到共情共感,找到律動,那令彼此感到與世界連結的詩,其實也不一定得在課堂或是學術裡尋找——沒有什麼是非怎麼樣不可的。
柔軟,大概也就是在遇到過不去的坎時,找到一個能將自己輕輕放下的方式。
・
疫情席捲時的春天,開始寫網誌,像是把自己緩緩托展開來。對於是否要離開學術圈,或是拿完學位後要去哪裡、能去哪裡,也有了不一樣的想法。跟系上好友M聊到彼此的心路歷程,才發現原來我們從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能留下來或是離開後要去哪,而是撕掉了學術標籤,我們究竟是誰?除了成為眾所期待的學者、評論家,我們對自己有沒有其他的期待,其他的想像?
我們究竟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些提問,是在原本的路途上無法想見的,卻在我被迫轉彎、停留的時候預言般地出現。我跟M說,怎麼樣都還是想要當一個寫字創作的人,持續地閱讀、聆聽,然後造出自己與這個世界聯繫的橋樑。時常會想,如果沒有出版、沒有發表,沒有大量的讀者,一個寫作的人還能算是「作家」嗎?「作家」一定需要各種文學獎項或是出版品來肯定嗎?還是,僅只是寫著,時而自剖,時而觀察,不斷探觸自己感知邊際,誠實真切地寫著,也就夠了。
上個星期過了冬至,煮了一碗熱呼呼的紅豆湯與芝麻湯圓,最長的黑夜已經過去,從現在起,只會有越來越多的光。2020年過到今天,充滿了褶皺與轉彎,被拋擲出原本的路徑,卻也因此發掘的自己不同的面相,也意外地發展了新的興趣。28歲這一年,開始認真學日文,做室內運動,嘗試烹煮各式料理,接觸了縫紉與塔羅牌,並且重新經營寫作。看不見盡頭的隧道裡,原來還是有點點螢光,自己,充滿許多可能性。要記得這件事情。
・

從朋友送的貓咪主題塔羅牌裡抽一張牌,問的是該以什麼樣的心情收束這一年。這一組可愛俏皮的塔羅牌組是來自好友S的生日禮物,提醒著自己時時被關心著,許多看似沒有了的事物,仍然不斷地在積累生發著。生活也是,情感也是,未來也是。抽到了方向朝上的女祭司,迷你逗趣的說明書裡寫道:The High Priestess card depicts a world fertile with possibility and power, as suggested by the symbols of moon and water. The candles represent darkness and light, secrets and clarity; the curtain conceals what, exactly, is germinating. Whatever it is, it’s catnip to you. Surprises are much more fun when you know they’re good.
原本肅穆端莊的塔羅牌,原本象徵神秘與寧靜自省的女祭司牌,如今變成一隻豐滿黑貓,搭配著圓圓貓掌無法拿起來的玻璃燒瓶與蠟燭。秘密圖騰變成貓咪最愛的貓草,驚喜不斷。變換了原本的意義與圖示,沒有什麼是非怎樣不可,黑貓後面的簾幕就像是要為這個迂迴的年拉上一樣。藍色月亮與深沈黑夜,暗與光,秘密與諭言,就算是幻覺,還是想相信下一個年會跟今年一樣充滿可能與重生。
每一天,都要練習把自己輕輕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