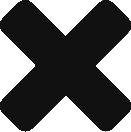文|張依婷
女人迷 Womany 2019/01/07
在美國的大學談台灣平權公投,從外國學生的問答間探究台灣殖民政權與性別平權的關係,儘管無解,但是我們不能放棄持續探究。
美國感恩節假期的最後兩天,台灣的九合一選舉與公投剛結束,同婚以及性平教育公投紛紛沒有通過。同志朋友們以及挺同社群覺得詫異又悲傷,網路世界一片哀嚎。以民主開放為傲的台灣,如今將人權訴諸暴力的多數決。
在賓州中部鄉下的我,追蹤著台灣的大選新聞,覺得憂傷,卻沒有太驚訝。今天站在挺同方的我們,對抗的不單純只是下一代幸福聯盟或是護家盟這些資金龐大的反同團體,更是多重殖民下所沿襲的性別性向文化與知識觀。我們所經驗的、所認知的,是各種歷史事件、政治角力之下的產物,等待今日的我們傳承,或是改寫。
大選之後,一同雙主修婦女、性別與性向研究(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的朋友L請我去他們的媒體與性別多元文化課堂上課客座演講(L是廣義的跨性別者,使用 they / them的代詞作為稱呼)。我跟L說我想講台灣的同志與多元成家的運動,當然不忘討論最近的五項相關公投。
L的課是大眾傳播系與性別性向研究所和開的課,使用的是一間能坐滿八十人的大教室。這門課有別於以往我教的大一小班寫作課(約二十四人),學生們從大二到大四不等。也因為課程強調多元文化的關係,許多學生抱持著較開放的心胸前來,班上族群的分佈也較我以前教的必修寫作課多元。除了白人以外,也多了許多黑人女性、拉丁美洲裔以及亞裔的學生,當然也有幾位國際生,其中以中國留學生居多。

圖片|作者提供
面對美國人為主的聽眾,我一直在想要怎麼呈現這個複雜的議題,因為我既不想過於簡化台灣的歷史背景跟性別性向議題的複雜性,同時也擔心班上多數的美國學生無法一下子接收龐雜的訊息。再加上我知道班上一定有中國的國際生,我雖然不怕冒犯他們的價值體系,但也希望平實真誠地解釋,端呈現實複雜,讓不能同意我的人嘗試傾聽。當然,他們都是學生,而我愛我的學生,我喜歡創造可以溝通的環境。
課堂一開始,我就告訴學生情境(context)的重要性。所謂情境講的是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變因所造就的特定時空與環境。當我們談論一件事物的情境,我們當極盡所能地瞭解文化、歷史、政治經濟成因,而不是以西方的價值或理論作為度量一切的標準。探究情境很重要,因為在美國與西方世界眼中,在我的學生們的心目中,台灣——一個他們可能沒有聽過的國家—與大部分的亞洲國家是等待被救贖的他者,等待追隨西方世界的腳步。
我說,台灣及亞洲不需要被西方自由主義救贖,即使是同性戀的議題也是,但我們的複雜歷史成因需要被仔細探討,我們需要去建構解釋台灣當地性別、性向議題的語彙。所以我問學生們,你們想像中的台灣是什麼?一位台裔美國學生舉手回答,提到了國共內戰與蔣介石。作為一個台灣籍的老師,不免擔心這樣的問題牽動班上台灣或中國的國際生的敏感神經。但我想正是因為這是一個敏感的議題,牽動著層層歷史以及各方價值觀,就算問題本身不能被解答,也有探問的必要性。我想,有時候勇敢面對問題的複雜,比追求答案、簡化答案還要重要。
「台灣是什麼?」這個敏感問題開啟了關於台灣層層殖民歷史的討論,關於我們今日對性別性向的認知是如何受到這些殖民政權的影響:荷西時期傳入的基督教 ; 日治時期的近代衛生系統與日本帝國當年引介的西方生物醫學、性別性向概念 ; 國民政府時期的儒家思維與國族主義 ,當然還有資本主義之下定義的異性核心家庭作為經濟生產單位等等。我們也討論了台灣當今的執政黨為什麼不能公開表態支持同婚,因為台灣在國際身分模糊的狀況下,民選政府必須鞏固選票與政權,這是許多近代國家建國時需要面對的難題,也是業障。為了塑造一個社會大眾都能認同的「正港台灣人」,不能夠符合主流社群的弱勢族群總是被犧牲。
在多重殖民與層層權力體制之下,今天我們在台灣討論性別性向多元,這樣的舉動能不遇到多重阻礙嗎?我們能不痛苦嗎?
然後我給學生講了釋憲還有反同及平權公投。除了一起讀公投選票上的條文翻譯,我們也一起看了下一代幸福聯盟官網上醜化同志遊行的圖文,還有他們反對同志教育的影片。有趣的是,下一代幸福聯盟用了一個美國反同教育的廣告,班上一位黑人女同學舉手說:「影片裡都是白人啊!」
我們接著討論了為什麼美國的原住民,亞裔,拉丁美洲裔及黑人都沒有被呈現,而這樣種族呈現單一的影片在台灣「護家」情境下播放的意義。一部幾乎都只有白人的影片,符合多數台灣人對美國文化的認識與期待,當下一代幸福聯盟使用這樣的影片提倡反同文化時,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了白人至上的種族意識的散佈與建構。
課堂接近尾聲時,我讓學生看了公投的結果及不同縣市的選票分布,討論了資訊流通對結果的影響,也試問:我們能夠說投下反對票的就是落後、就是惡意、就是敵人嗎? 還是我們也必須考慮城鄉差距、資訊釋讀、教育普及、階級差距、生活經驗不同?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未投票率怎麼解釋?我告訴我的學生,我阿嬤說她沒投公投,因為她看不懂選票。
雖然我們不能完全回答這些問題,但問題的本身透露了公投的程序以及被公投的議題的混亂複雜。資訊氾濫的年代,我們習慣避開複雜的物事與成因,將結論二分,並用這樣的結論來分辨敵我。透過這些問題,我希望我的學生們嘗試思考物事之間的交錯關聯。有的時候,所謂關聯並非直線性的因果關係,而是多重歷史、政治積累之下的結果。也許我們不能成為解決所有問題的人,但或許能盡力嘗試做一位細心謹慎的探問者。

圖片|作者提供
最後,我給學生們幾個討論問題,包括公投作為決定多元成家和性教育的媒介的適當性。孩子們表示不解為什麼人權議題會淪為多數決,然後為什麼複雜的文化歷史、深刻的情愛感受,是用是非題決定。
我們也討論了「家庭」的重新定義,我請他們分享自己說服反同方的經驗。有位白人女生說:「根本不可能說服,因為對方不願意聽啊。」相互傾聽多麼重要,卻又多麼與人性的鑽牛角尖相背,多麼不可能!
我們的課堂討論就在這樣的無解中結束。無解令人痛苦,但我更害怕簡化問題。如果有什麼所謂對世界溫柔或善待世界的方式,其中應該包括對事物抽絲剝繭,不追求單一或是二分的結論,腳踏實地探求,不走捷徑。
雖然我們都希望能夠尋求解答,我們也不該忘了,不只是同志朋友,還有許多雙性人、跨性別者,都是在無解之中生存的人。 若我們祈求「做得更多」,其中一部分當從力求事物呈現精準的教育開始。 而我希望這樣的教育方式以及對待問體的態度,能慢慢被接納並擴散開來,在台灣或是台灣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