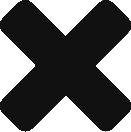長大就是一個逐漸體會自己的極限的過程。不再有青春那種希望無限、精力無窮的籌碼,所以開始懂的休息,在喧囂的世界裡畫一個能夠從容自處的圓圈。最近,我的圓是《邱妙津日記》,當我覺得自己被掏空的時候,不能再多給予這個世界以及身邊的人更多的時候,我去讀邱妙津20歲時寫的日記。也許一次只能讀一個篇幅,卻像是走在一個通往有愛的未來的道路上,思索創作,重新檢驗一個現代社會與體制對於成年人的期待,也再思量如何在多重的期待與標籤之下以創作,持續餵養自己的靈魂。
1989年七月,滿20歲不久的邱妙津已經將藝術與創作當作她的指引,既是志業,也是她生命的原動力。在日記裡,她寫道要將自己寫作的「質」與「量」提升,同時深化自己的文字豐富程度,而所謂的豐富,仰賴的是自身生命的層次與厚度的積累,將生活裡的窄仄寬宏、荒謬不仁都寫進靈魂裡。在一個沒有現成的語言談論自己的慾望與性向的年代,在一個自己的意念與資本、生產為導向違背的社會裡,創作是邱妙津存活的方式。提出異議的同時,愛與意念向著她內心嚮往的忠誠噴射。
在冰冷嚴苛的體制裡,我發現自己時常回到邱妙津用慾望與文字豢養的情感境地,持續感受著書寫與閱讀所激發的溫度,即使我們身處的時空背景、表達方式與對話對象都是如此的不同。我時常覺得,論文的書寫雖然與創意寫作大不相同,卻也需要極大程度的真誠,才能讓寫出來的每個字、每個句子有溫度與實感。
論文的書寫能夠與創意寫作相提並論嗎?其實大學時期,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缺乏想像力與創造力的人。我無法成為文學的創作者,因為我的頭腦裡沒有故事。我對閱讀本身非常有感觸,好像每一次與文字的接觸都是千萬意念的生發,奇形怪狀的文字在腦海裡迴盪成聲音,不同的人聲又變成複雜的樂音,有的是和諧共鳴,有的是轟隆巨響。我追隨著文字在腦海裡造成的樂音,想把衝擊與感動以評論的文字寫下來。我的頭腦裡雖然有許多對話,卻沒有畫面,也沒有故事,也因此覺得自己是個沒有什麼想像力的人。
這樣的想法一直持續著,直到大三去北卡羅萊納州大交換的那一年,我跟Jon Thompson教授聊起這件事情。我談起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想像力,也無法成為文學創作者,但是老師以緩慢渾厚的聲音跟我說,閱讀與評論本身也需要巨大的想像力,才能夠在理解文意之後,做出深刻又細緻的詮釋。我一直惦記著這段話,卻是在多年以後,開始寫自己的論文時,才更加確立了這件事情。
有時候,做研究與發展論述就像是創造故事,在汲取多方的材料與元素以後與過往的、現存的世界對話,同時又建構一個新境地,一個自己不曾到達過的地方。以前曾經跟系上好友M聊到這件事情,她說那個我們「不曾到過的地方」不一定是多麽新穎的所在,而我們想去的那個地方、想回答的問題,或許已經被好多人回答過了,我們畫出的地圖也不是大家所認為的原創獨特。其實,從來就沒有所謂「原創」這件事情,但是藉由我們的想像力還有生命經驗形塑出來的境地對我們自身而言即是最獨特的。如果能夠將我們所思所想寫下來,分享出去,我們透過學術研究所發出的聲音,也將成為別人前往他那獨特所在的一片風景、一條線索。
過去這八個月的論文創作裡,不時讀到令自己動容的學術作品,它們不斷地改變我對於評論與創作的想像。在領域分化、標籤分明的學術文化裡,我發覺那些令我怦然心動的作品,不一定在主題或是立論上有所新意,卻能在引用物事與論述時,擺脫領域建置的限制。作者膽大心細地撥動著、牽引著不曾交集的理論脈絡,帶著讀者前往看似熟悉卻陌生的境地──那境地所指的是一個研究者介入這個世界的方式。
誠實面對各式領域條件與限制的學術書寫總是充滿稱命力,像是蔓生的花園。它們將看似無關或是因為知識化分而不能交集的沉思片段串接起來,為許多不能回答的難題,提出充創意深刻的省思,並以一個作者獨特的聲音傳達出來。我喜歡著眼於一位書寫者的引用與方法,好像他們所包含的、借用的也透露了他們的知識境地的形成以及他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如果帶有極大的誠意,我們的書寫方法與引用,也反映了我們靈魂的形狀與顏色吧。
以前不是很明白所謂評論與學術的創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覺得大環境迫使之下,周遭的人們也急著為自己貼上各式領域與理論的標籤,自己也跟著這麼做。在還沒看夠世界的知識與精神圖景的全貌時,我就已經在分割它們了。寫論文的期間,重啟自己對於閱讀與它們在腦海裡造成的樂音的熱愛,不再分割知識,僅是汲取,編織,然後延續自己所信的物事的意義。
雖然我對創作的反思來得有點晚,在27歲的交叉路口,沒有邱妙津當年20歲的澎湃激情還有對於藝術的熱烈執著,但卻想在這個人生難得自主的階段培養自己的創作品味。在一個推崇大師與權威的年代,我時常想著有沒有可能不再仰賴這類的標籤作為我們創作與吸收知識的單一指標。也許我們都能孕蘊自己的方法論,編織物事,餵養靈魂,不斷深化自己聆聽世界樂音的能力。曾經戰戰兢兢,害怕與社會還有體制的規範不相符,如今在一個看不見未來的慌亂年代,好像也不那麼害怕了。
在一個嚴苛的世界裡,開口就是生命、靈魂什麼的,好像顯得太爛漫了。不過眼前所見是荒涼貧瘠、弱肉強食的環境,身體時常感受到的是各式疆界的強化,我在乎的就是怎麼在一個愛的空氣稀薄的世界裡活得好好的。在體制與規範裡游泳,時常覺得不管離什麼樣的岸邊都有點遠,我因而喜歡咀嚼邱妙津所說的「精神縫合感」: 一種以「痛苦和人性裡極大的天真製成」的,「甚至是文字世界裡才會有的。」那大概就是一種覺得自己所內裡的每一寸肌膚、毛髮都被接納,不再被體制與期待分化切割親密感,像是被世界輕輕托住一樣。
每一次的創作,哪怕日記裡的、研究與評論的、或者是閱讀的當下所生發的,都離那樣的精神縫合感近一點點。只要還有一點點蠢蠢的天真殘留的話,即使泅泳時不能靠岸,也不至於在看不見邊際的冰冷海水裡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