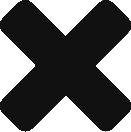作者 張依婷
獨立評論@天下 6/6/2020 |原文點此
讀李維菁的散文與小說,不難發現在她的文學宇宙裡,創作與生活相互依傍,不講傳統文人推崇的超脫世俗,卻向生活的質地裡扎根,即使所謂生活即是在對事物有所鍾愛之時,又有無盡的自我厭惡;是遭受性騷擾與歧視的憤怒當下卻無能為力;或是超時工作活得不成人形時,卻繼續臣服於體制,成為那偽善的自己。
2019年出版的《人魚紀》裡,李維菁以國標舞為主軸探索都會的女性生活經驗,誠實面對藝術體驗與生活之間的緊張關聯。小說探討父權社會裡的兩人配對、異性邏輯,思索身體在各式權力網絡裡泅泳的同時,也捕捉個人對生活的熱情所製造出的繽紛浮光。
跳國標舞的人,永遠處在沒有舞伴的恐懼中
李維菁的「人魚」承載了許多意象:她是主角夏天的化身,是對於國標舞綺麗舞姿的比喻,象徵著色彩與流動的同時,又具象化那在陸地上片尋不著同類的寂寞感。在安徒生的童話裡,人魚公主為了愛情以自己的聲音作為代價,換得了讓魚尾消失的藥水,在陸地上行走的每一步都痛如刀割。《人魚紀》承接著人魚在陸地上的生活,不為愛情而來,卻渴望在人類的世界裡學會走路,順暢地、穩穩地走路。寂寞時,就去學跳舞,即使舞蹈作為人魚理解世界的方式仍充滿衝突與困惑,還有許多不能被他人回應的渴望。
李維菁筆下的國標舞是主角夏天快樂的泉源,習舞的人生像是「細細碎碎的片段串珠織成」,飛揚的裙擺與與充滿力量的舞姿讓人「從靈魂內部發出嘆息。」對舞蹈藝術的熱情造就了夏天生命的原動力,但也是在國標舞的世界裡,她見證了舞蹈、身體、生活的密不可分,伴隨著極限興奮的,是身體彼此之間的依附與暴力。向上飛揚的同時,也是墜落。
在舞蹈教室練習的每一天,都像是喚醒身體律動的記憶,然而任何精妙舞姿與暢快瞬間最終仍受制於國標舞本身的異性與雙人配對邏輯。小說的一開始,李維菁就告訴我們「跳國標舞的人永遠處在沒有舞伴的恐懼中」,由舞蹈生發出的快感與藝術一定要有舞伴來成就,舞伴之間又必須是異性的搭配,「男生」領舞,「女生」跟隨。國標舞教室裡,人們成雙成對,找不到舞伴的人誠惶誠恐,找到舞伴的人又得練習跟舞伴磨合。舞伴之間若不能相互支撐,結果便是兩具身體相互拉扯;即便是看似已經磨合的身體,也常常是一方支配著另外一方。舞伴們之間的關係,反應了各種心緒:支配他人的渴望、害怕形單影隻的恐慌、病態式的自負、沈默的自我貶抑與屈就。
雖然兩人一組的關係很有可能變得兇殘暴力,李維菁也點出了我們對於成雙成對的渴望,那就像是人性最脆弱之處:「彷彿自己專屬於誰,或誰專屬我,我有自己擁有的舞伴的安全感,胸中湧起和世上另一個人成為一組的歸屬感。」
一個「正常」社會的邏輯
雖然《人魚紀》著眼於國標舞裡的雙人成對以及其造成的撕裂,更令我深刻的是李維菁對於異性戀邏輯的省思。所謂「異性戀邏輯」講的不只是異性戀作為性向的唯一指標,與同性戀互斥;「異性戀邏輯」更是一種生活型態以及價值判準,例如我們從小被灌輸的擇偶方式。無論是外表、儀態、階級與背景,所有的標準都指向所謂「適當的配對」,用以鞏固婚姻與家庭的組成,「正常」的社會進而能被繼續複製與運行。
異性配對也是國標舞的精神本質: 男人的職責是保護女伴不在擁擠的舞池裡受到碰撞干擾,而女伴則「以男人為中心,等待男性的指示,啟動自己的身體。」 透過夏天對於國標舞世界的觀察,李維菁試問:是不是要能夠浸淫在國標舞這種「本質上精神上就極度異性戀沙文的世界」,相信它的異性戀邏輯,才有可能駕馭這樣綺麗繾綣舞蹈?
《人魚紀》的迷人之處,在於它透過國標舞去探討讓「正常」社會持續運作的異性戀邏輯,同時又從本質上去解離許多看似天經地義的人際連結。讀者們可能會認為李維菁筆下的人際關係過於灰暗,她的角色們充滿缺陷,甚至病態,例如控制欲極強的母親、沒有自我的女兒、狂暴的男友、冷漠的父親、自負的少年,彷彿生活即是人際之間的相互拉扯與制約。沒有歸屬,更沒有愛。
書寫家庭時,李維菁直接道盡了家庭作為物質世界的生存隊伍所產生的荒涼感。如果家庭是引導我們進入常規社會(如 「成功」、「買賣」、「安全感」、「伴侶」)的地方,主角夏天所見證的家庭是一個家人「情感充沛,卻無能與人連結,也無法同理他人的孤單」場域。家人們活在各自的世界裡,從來沒有毀滅性的斷裂,卻也無緣相知,「生亦如死,死也不散,只是不聚。」
以被扭曲的身體,繼續尊嚴地行走下去
這樣的書寫,或許會被認為是過於憤世嫉俗,好像在解離了國標舞、家庭、人際連結之後,沒有愛的餘地。的確,《人魚紀》不著眼於常規社會裡的人情溫暖,歌頌的是那些被邊緣化的身體:
女性身體、老化的身體、跨性別身體、寂寞的身體,還有他們在生活中承受的羞辱與與撕裂。被摧殘制約的身體,與小說中的綺麗的「人魚」、「舞蹈」意象形成強烈的對比。對許多人而言,這種無愛、無所依歸的巨大荒涼感,不是憤世嫉俗,只是太過日常,太過真實而已。
雖然對於制約身體的常規邏輯毫無保留地批判,《人魚紀》整本書也不斷地在改寫我們對於身體、生活、性與性別的認識。看似寂寥的世界觀,實是李維菁緩慢平穩地重構一幅為愛充盈的圖景。
例如,書寫「性」的意義時,李維菁在小說前半部不斷強化「性」是二元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標記,是人們對於女性身體厭惡與渴望的來源。在厭女的異性戀社會裡,女性身體的意義是其性別,而「性別唯一的意義,是性」,是生殖力,是歡快也是噁心。然而,李維菁最終翻轉了性與性別的可能性,她書寫男扮女裝的老房東與鄰居男孩,寫男孩穿著鵝黃碎花洋裝時散發出的女性化的氣味。她也書寫一位單純寬厚的少年,每個禮拜花一個下午的時間與自己好好相處,在午後陽光曬得發暖的房間裡,「緩慢而札實地自慰,是善待自己的純然愉悅。」李維菁告訴我們,性應該是「善待自己,是愉悅,不是痛苦的來源。」
就在李維菁重構性的意義時,她也重新詮釋跳舞這件事情。曾經是為了那「向上的渴望」與「極限的興奮」跳舞的夏天,在舞蹈世界裡終遍尋不得舞伴,最終明白跳舞其實是平穩地掌握自己的重心,將雙腳穩穩地踩進地裡,「踩得越深,越能自在漂亮地向前進,或往後退」。跳舞於是自向上飛揚的興奮中抽離,成就了向下札跟的盼望,用雙腳支撐自己的身體,「漂亮地走路。」
李維菁對跳舞的詮釋,似乎回應了她對於創作的理解:它們都不再只是形式與熱情的展演,亦是個人回應生活與世界的方式,哪怕是以受過傷的人魚雙腳走路,或是以被生活腐蝕的靈魂殘喘書寫著。短短兩百多頁的《人魚紀》是作家與這個世界的聯繫,不逃避人間困惑,卻直視身體之間的暴力與依附。李維菁似乎告訴我們,透過一次又一次地直視,我們又離順暢走路的樣子近了一點點。
也許,像《人魚紀》這樣的作品,會被狹義地歸類為「女性文學」,或是被輕易斷定為格局不夠宏大。然而,對於人際關係深刻思索,解離其背後的社會常規制約的李維菁,是暴力不曾終結的世界裡需要的聲音。最終,李維菁沒有讓人魚的聲音被奪走,我們聽見了她的吶喊,是那樣誠實而堅毅。在這樣強迫雙人配對、異性戀邏輯、父權當道的社會裡,沒有人不是受傷的,而李維菁像是在說,我們需要的是更多自愛的勇氣,才有辦法以被扭曲的身體繼續尊嚴地行走下去。
書名:人魚紀
作者: 李維菁
繪者:Whooli Chen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5